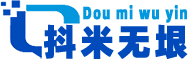寫作什么樣的小說作品好?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02
一個勞作了近半個世紀的寫作者,也會是一個勤奮的讀者,在漫長的文學生涯中,肯定有許多感觸可談。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生人會有特別的、屬于自己的經歷,這大概是很難重復的記憶:童年饑餓,求學困難,“上山下鄉”和“文革”等,一路走來的許多重大社會變動跌宕,不可謂不大。后來又是對外開放時期,是商業化網絡化時代。文學在劇烈起伏的社會思潮中演變,高潮低潮,前進倒退,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楚的。
記憶中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,一年最多出版三兩部長篇小說,散文和短篇小說集也只有不多幾部,文學刊物少極了。能夠從事寫作和出版的人只有不多幾位。所以那時候這些書籍和這些作家,影響之大無與倫比。現在許多人還記憶猶新,甚至以那個時期與今天作比,認為現在的文學和作家影響力小得多,因此遠不如那個時期更有成就。這種毫無理性的言說竟然獲得了一些贊同,可見昏聵。當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基本上截斷了外國文學輸入,同時禁止了大多數作家的寫作權利,那么僅有的一點“當代文學”想沒有影響都做不到。這不是一種正常狀態。實事求是講,如果按起碼的詩學標準來評判,當年那些影響巨大的文學出版物,相當一部分極為粗陋拙劣,連基本的文從字順都做不到,又何談“文學”?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《古船》,張煒著,人民文學出版社(首發于《當代》1986年第5期)
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,作家們重新獲得了寫作的權利,年輕作者紛紛涌現。被壓抑的精神突然得到釋放,無數意見得到表述。這是傾瀉般的語言洪流,與之匹配的就是大量文學雜志。出版社也十分活躍,古今中外各種作品得以面世。此刻的文學仿佛具備了一種呼風喚雨的力量,影響之大簡直空前。人們第一次感受到文學的強勢存在。一個作家發表一篇作品便可名滿天下,全國上下爭讀一部一篇、街頭巷尾口耳相傳一位作家,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書籍的印刷量大極了,幾十萬上百萬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。
那個特殊的時期,人們已經習慣了從文學作品中尋找答案,文學既是教科書,又是訴求狀,更是呼吁文。大家積壓了幾十年或更長時間的激情、痛苦或欣悅,都堆積和貯存于文學之中。那些長期封閉和沉睡的一部分審美力,這時候也一并呼喚出來。總之文學喊出了許多心聲,讓人獲得前所未有的審美愉悅。但后者是初步的或退后一步的,人們得到的欣悅主要還是社會道德層面的。當然這也與審美連在一起、不可分剝。
那是一個長長的文學狂歡節。在這個節日里,寫作者和讀者都是深度參與者,他們將把這種激越長久地保留在記憶中。
03
轉眼就迎來另一個時期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,文學寫作和閱讀狀況急劇改變。一方面原有的社會表達已經沒有了噴發態勢,另一方面無數的文學品類蜂擁而至,讓人猝不及防。外國文學加快輸入,各種文學實驗和模仿日益增多,各類出版物比以往多出幾十倍上百倍。就文字本身而言,花色品種及數量已經超出了幾代人的記憶。寫作者要適應版面的擴張,一時泥沙俱下。人們不得不接受讀物泛濫和選擇困難這樣的現實,目不暇接,一部作品引起轟動的情形絕無僅有。文學作為一個話題正在冷卻,由視野的中心漸漸移向邊緣。
從專業角度論,“邊緣”說當然是不通的。因為文學只能置于審美的位置,它從不屬于行政律令,當然沒有令行禁止的功能和使命。就現實的有效性來看,文學在人類歷史上從未處于“中心”。審美依從心靈,屬于生命感奮,也只能裝在心中,而“心”這個器官一直處于身體的“中心”,所以說文學永遠不會退到“邊緣”。審美具有差異,一個地區或族群之間的區別很大,它將決定野蠻與文明、完美與粗拙,更有創造力的不同。文學當然會讓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具有精神的優越性,讓其變得更自信和更有力量。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隱隱地希望文學具備強大的號召力,甚至法令一樣的現實規定力,這不僅幼稚,而且是對所有藝術的誤解。正像文明本身需要日常的證明與注解一樣,文學也同樣如此,它是更加寬廣的事物,包含日常并溶解于日常。它將化為無數小項和分項,呈現于生活中。也正是平時那些細小的事物,輻射出文學的功用和力量,我們可以說,它們的痕跡無處不在。
有人曾經設問:“‘文學’是不是‘文化’的核心?”這算是大膽一問,但真要回答卻需復雜的論證。不過幾乎可以肯定,文學一定是文化傳承的核心部分。回望歷史,離開詩書典籍,一個族群的文化精神載體就要去掉大半。沒有詩,沒有散文和小說,我們的文明何以傳承?歷史上不斷發生巨大的社會動蕩,外族入侵,吞并中原,整個民族的治理體制一再更迭,最后起到統一作用的決定因素還是文化。文化不僅維護了文明的版圖,而且維護了地理的版圖。文化版圖的核心是文學,這是不爭的事實。從這個角度講,文學不可能退居邊緣,它一直牢牢地植于思想與心靈的中心。
在網絡時代,寫作和閱讀方式發生了改變。人們開始熱衷于碎片化閱讀,在小小屏幕上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多。內容蕪雜,主要是社會信息的流動。人類的好奇心首先需要得到滿足,審美也就放到其次。人們愿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更多消息,雖然大多無關于自己。它們作為意趣而不是意義被人接納。這就占用了大量時間,受到傷害的不僅是文學閱讀,而是整個的精神空間、生存空間。
這種特異時期形成的視覺侵占引起了普遍的憂慮,這不光是文化的憂慮,而是更多方面的擔心。一旦深度滲透的數字生活走向了極端化,我們也就失去了深入關注事物的能力和機會,而所有的創造和發現,都離不開這種關懷力和探索力。我們不再專心,而審美力是更高一級的,它即將渙散。最可怕的是生命品質的改變,是集體無意識地陷入輕浮和草率,喪失理性思考力。這最終引起什么后果,似乎不難預料。可見數字傳播引起的改變,已經遠遠不是閱讀本身的事情。同理,也不僅僅是文學本身的事情,它關系到更本質和更久遠的未來。
04
碎片化瀏覽占據整個閱讀生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,這種趨勢還在加重。智能手機的危害與功用同在,隨身跟命,不再分離。人們不分場合地使用,在候車候機廳和一些休閑場所,甚至是會議或行走中都在滑動屏幕。人幾乎不能讓眼睛閑下來,也不能沉思。屏幕上的閃爍跳躍具有傳染力,會像病毒一樣入侵,讓我們上癮,產生從未有過的依賴。我們從此把與生命同等寶貴的時間耗損一空,卻少有回報。
大量的電子片段堆積在大腦中,損害無可估量。某種神經依賴癥一旦出現就無法治愈。說到現代科技帶來的便利,那是另一個話題,就讀取這個單項來看,它造成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。無法阻止的流言,難以辨析的消息,聳人聽聞的事件,淺薄與惡意,淫邪和罪愆,都在小小熒屏上匯集。欣悅少于沮喪,絕望大于希望,人一天到晚淹沒在極其惡劣的心情和接二連三的恐懼中。這里流動的文字大多是即興的、未經打磨的,語言品質之低下,心緒用意之陰暗,幾成常態。這種氣息熏染下的精神生活使人向下,而不是向上。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生活中的認真態度需要嚴謹的文字去培養,失去了起碼的語言標準,社會精神就會淪喪和消散。至于文學,它要求更多的接受條件,比如相應的視覺觸及方式。傳統閱讀通常為紙質書,它經歷了從宣紙木刻到現代印刷線裝膠裝,質感已經變化很大。很早以前的線裝書舒放柔軟,變為西式書籍的挺括,也產生了感受差異。即便是現代印刷,從鉛字排版到激光照排,讀者也需要適應。
就文學欣賞來看,熒屏這個窗口未免太小。主要還是質地的改變,這與書寫效果相去太遠。聲光技術的遙不可及,阻隔了人的情感。我們雖然在讀文綴句,意思也能明白,但總有一種不夠踏實的感覺。文字和書是這樣成形的,先是寫于樹葉和龜板陶片,進而是棉帛和紙;筆由動植物身上取來的材料做成,最后才是鉛筆鋼筆。人的情感一筆筆記下,手工連接的心思有一種天生的淳樸,感染力代代延續;直到印制成書裝訂起來,其物理還是接近原初。而今通過無線信號接收數字,于掌中演變成形,走得太遠。一種無法言喻的飄忽感,很難在心里植根,來去匆匆,像一層灰塵,輕輕一拂就沒了。
就語言藝術享受來說,看似小小的區別,后果卻是嚴重的。有人說這種很難察覺的差異會在習慣中克服。可是不要忘記,這個根性深植于生命之中,不可能在一代或幾代人中改變。我們的閱讀方式延續了幾千年,人眼適應反射光歷經了幾萬年的進化。
在閃爍的光標下,文字的判斷力會出問題。事實上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,對語言藝術的誤判這樣大,有時大瞪雙眼就是分不出拙劣與精妙。我們對語言變得遲鈍,實際上是麻木。詞匯在機械連綴和光電運行中失去了生命。就文學來說,這種損傷是根本性的。
05
由于語言的使用趨于機械復合的性質,所以人人都可胡亂堆砌。即便在一些莊重的場合,也經常看到草率幼稚、根本不通的書寫。人們已經沒有審慎操練語言的意識,更不會發生生命的關系,只是程式化地、無關痛癢地使用。
一般的文字工作是這樣,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則產生了災難性的結果。我們如果稍稍注意,就會發現隨處都是文字垃圾,它們正日夜滾動在屏幕及各類印刷物上。興之所至的涂抹,昏妄的囈語,不知所云的喧嚷,以及惡意的發泄,晦暗不明、意思曖昧、稀奇怪異,全都出現了。正常的人只要耽于這種閱讀區區十分鐘,就會心生感嘆:怎么會有這么多無聊、陰暗丑陋和惡意?美與善何在?它們仍然有,可是已遠遠不夠,難道在堅硬的金屬容器中密封起來?污濁和拙劣與一個時期的商業主義和利益集團結合,運用金錢向前推進,生出椎心之痛。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語言藝術最后連一個口實都算不上,在一部分人那里只是胡言亂語的代名詞。需要垃圾填充的版面太大,以前是紙質的,現在則是由無限量的光電承載。胃口無限,可以連骨帶肉吞下去。所以現在需要一大批喪心病狂的人,去做人世間最不堪的營生。
中國古人有一個說法,叫“敬惜字紙”,說的就是對文明承載物的尊重,這表明了一個民族的高度文明自覺。而今既已如此,其他也就不必奢談。什么“未來”之類,它不屬于我們。
縱觀歷史,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:從未有如此多的人參與涂抹。幾千萬人從事廣義的“文學寫作”,歷史上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。有人不愿正視這個事實,好像一切照舊。散文,詩歌,書評,短篇、長篇,各種題材和體裁相加,多到前無古人。各種文字像潮水一樣涌來,不是目不暇接,而是直接淹沒。無論是網絡平臺還是紙質媒體,文字的潮汐無時無刻不在涌動。午夜和凌晨都有新作發表,黎明時分已閱讀十萬,跟帖八千,不知刷新了多少次。“文學”洪流滔滔不絕,與其他文字一起洶涌。敏感一點的作者和讀者,面對此等情狀可能覺得恍若隔世。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這么多人參與“文學”,還能說文學“邊緣化”?如果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,那時只有三兩個作家和三兩部作品,某些人也視為盛況,而今這一切又該如何評價?即便回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,雖然寫作者和閱讀者成倍增加,但比起現在也只算個零頭。有人會說那些只有三兩個作家的年代,人數雖少影響巨大。是的,不過如果把文學比作一場體育賽事,賽場上只允許兩個人參加,那么這些選手想拒絕當冠亞軍都難。
實際上就是如此,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,無論一個“選手”天資如何優秀,都不準上場。要談文學的“中心”和“邊緣”,那時候的文學才真正退到了邊緣。今天的一些人之所以把“邊緣”掛在嘴邊,是因為參照出了問題。只記住某位作家引起的巨大反響,卻沒有分析這種影響緣何而生。千萬人寫作和三兩個人寫作,毫無可比性。
在萬馬奔騰的寫作中,文學關注力的分散和瓦解,是一定要發生的。
06
事物變化的速度和幅度,在不同領域里差異很大。新科技發生遽變,有關數字產品的刷新頻率快到驚人。在我們的記憶中,從電視到智能手機,從電子圖書到閱讀器,再到大小網站、音頻視頻、微信平臺,文字與圖片的海量承載交錯重疊。這種類似的技術創新和形式遞進正未有窮期,考驗著人類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。
這一切與我們這一代記憶猶新的閱讀饑渴,形成了兩個極端。那時候要找到一本新書多么難,即便是東部沿海省會城市也只有一份文學刊物,甚至連這僅有的一份也曾停刊。這樣的經歷,四五十年代或部分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不陌生。這其中的一部分人至今仍然活躍,正深度參與當代文化活動,包括文學閱讀和寫作。他們并沒有退場,依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專業影響力。以前的道路和印象全不是空白,那是相當龐大的積累和貯備。經驗的再處理是一個極其沉重的任務,無論愿意還是不愿意,都要面臨著一次又一次的更新和蛻變。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由長期的生命體驗換取的認識無比寶貴,但的確陳舊了。有些結論來自另一個時代的參照,有些情感也屬于昨天,它們正在高科技時代里以加速度的方式后撤。今天必須正視的是近在眼前的這個世界,是別一種精神生態。僅就寫作和閱讀來看,作者與讀者共同面對的不再是兩三個,也不是幾十個上百個,而是歷史上從未出現的龐大群體。這些人魚龍混雜,以至于成為荒誕的聚合體。十幾年前有媒體曾刊過一條新聞,嘲笑西歐和東亞的某些國家,說那里幾乎人人都在寫作,個個想當作家。話音剛落就到了網絡時代,自媒體產生了,于是那種被譏諷的現象不是照抄和復制,而是在當地加倍繁衍:各個階層都在碼字,隨時隨地出版發表。這是人們從未經歷過的一個時代,讓人恍惚奇異,好像從人煙稀少之地突兀地空降到了人山人海中。
有人把網絡時代日夜翻涌的語言文字比作一場“沙塵暴”,透露出十足的悲觀和恐懼;也有人喻為語言文字的“瓢潑大雨”,比起荒漠里偶落的雨點,確像遭遇了一場傾盆大雨,大水漫卷之災令人惶恐。如果能夠再達觀一些,是否還可以有另一種中性的描述,比如想象我們正走進一片語言文字的“熱帶雨林”?這里是一個強旺生長的、繁茂重疊的世界,有各種各樣的動植物,各種各樣難料的狀況,更不乏巨大危險。這樣說似乎比“沙塵暴”和“瓢潑大雨”要準確一些,也較為直觀形象。
進入了這樣的“熱帶雨林”,那么所有的行進者都要提防了,要有相當過硬和周備齊整的行頭。因為這里有大動物出沒,有蜘蛛和蟒蛇,有葛藤和食人樹,還有藏了怪獸的沼澤水汊。當然這里還有美到驚異的花卉和果實,有驚人的繁殖和生長,高大的綠植鋪天蓋地。
聲明: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容,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,均為采集網絡資源。如若本站內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益,可聯系本站刪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