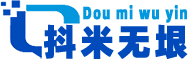網(wǎng)絡寫手寫作是否好生存?寫作的人多了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起點中文網(wǎng)截圖
每個寫作者都是這樣的“行進者”,他如果按照過去的方式毫無準備地踏入?yún)擦?可能連半途都無法抵達。他將從頭設計重新選擇,強化手中的器具,應對茂密的縱橫交織;扎好營地點起篝火,將利器打磨鋒銳;極其謹慎地行動,許多時候以靜制動,在合適的時刻出擊。方法和機會多種多樣,或是絕路,或是另一種生存。
一個心神篤定的寫作者不會在這樣的時刻放棄。他會再次出發(fā),開辟自己的路徑,而不會追隨潮流。一個經(jīng)過了漫長勞作,同時又親歷過諸多風云變幻的長旅者,自會冷靜堅卓。他會愈加嚴苛地對待筆下的每一個字,濾掉一切泡沫,壓緊每一方寸。身處這樣一片雨林,干練和警覺,操守和禁忌,還有必要的給養(yǎng)輜重,力求一無疏失。既不存幻想又遠離悲觀,與輕浮草率劃清界限,對誘惑保持最大克制。不堆積,不急切,不趨時,不彷徨,更不能困頓,不能在睡思昏沉中流出口水。
憑借熱情的青春時代已然過去,這里不是指生理年齡,而是說心靈的步伐。數(shù)字時代是使人加速蒼老的光陰,這時候尤其不適合稚兒般的躁動。時髦的追逐既無盡頭,又耗失中氣,最后什么都留不下。誰如果僥幸融入滾滾洪流之中,誰就早早地消失。停留,站立,久久打量,直到變成一塊化石。如此一來,在往復交織的潮流中就不易破碎和潰散。這讓人想到了一個老舊的比喻:每一位作家都如同一座精神的島嶼,如果由泥沙構成,即經(jīng)不起浸泡拍擊;如果是一整塊頑石,那就足夠應對眼前的潮水了。
必須具有堅硬的本質和錘煉精神。文學的表象即語言,要把它冶煉成一種鋼藍色。這是一個緩慢的、收斂的、緊縮和匯聚的狀態(tài)。最終形成強大的意志力,固化冷凝,以此抵抗迅猛的狂潮。一切急速追趕,踉蹌狂奔,都將倒在帶刺的葛藤下邊。在渾茫的陰影里必須止步,不要迷戀,不要倨傲;不要急躁,也不要散漫。把真正的價值放在時間里,卻又不能把時間當成敷衍的說辭。生存的彈性不能變成策略,而是要彎成一張弓,讓其具備強大的發(fā)射力。
07
一個寫作者當然會放眼于漫長的時間,但是無論多么高遠的功利目標,都不應該主宰自己的工作。如果說不為眼前寫作,不為當下的榮光和價值寫作,只把目光投向未來,即為歷史為永恒為不朽,那也有點空蕩和虛幻了。一切還需要敲打到細節(jié)和局部里去。因為凡事沒有說說那么容易,看起來光芒閃爍的大目標,也會是鑲了金邊的功利。一個寫作者最好的狀態(tài)還是先安靜自己,先讓自己滿意,先自回到心靈。在這個悲傷多難的世界上,還有什么比妥放自己的靈魂更為重要?這種自我注視和自我滿足,不自覺地就會將專業(yè)標準和精神標準設定到一個高處,那個高度,外部施予的善意和惡意都難以觸摸到。專業(yè)本位與讀者本位相比,前者當然更可靠一些。安寂快樂而又不乏辛苦地工作,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接近了最初的理想。既不為小功利,也不為大功利,而專注于個人職業(yè)生涯中生成的那個越來越平淡、實際上卻是越來越高聳的指標。
據(jù)說現(xiàn)在的某些網(wǎng)絡寫手一天敲擊一萬多字都不算快。有的一邊聽著音樂,就可以打出幾萬字。而人們經(jīng)驗中的書寫是鋼筆一筆一畫刻記,狀態(tài)最好的時候也不過每天兩千。這讓人有些疑惑了,懷疑這會兒是不是在談文學。是的,已經(jīng)走離了話題,這與文學沒有一點關系。但我們前邊說的既是“熱帶雨林”,也就包括各種異象,并沒有排除種種滋生和隱伏。這正是問題所在。時代變了,我們要一再提醒自己進入了全新的境域,這是一個立體交錯、眼花繚亂、怪異迭起、昏暗茂密的陰濕空間。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張煒手稿
而今人人擁有一個小小魔器,它被握在手中,時時對視,上面閃爍文字和圖形,消息趣聞及其他,應有盡有。內容差異大到天壤,獲取工具卻如此單一。這就帶來了無法調和的矛盾。思想深邃、風格迷人的語言藝術,只能是沉靜默守的獨對,是一次心靈相遇。它需要一種起碼諧配的形式,比如捧起一部紙質書。熒屏上的文字無論多么逼真清晰,仍然與深入的領悟相對沖,折損詩意,排斥幽思。
我們千萬不可任性,試圖借助一個小小的現(xiàn)代魔器進入堂奧,領略其獨有魅力。這不是面對經(jīng)典的態(tài)度,不是享用語言藝術的方法。
此刻的謹慎持重是必要的。閱讀作為一種生活的不能割舍,在任何時代都是相同的,不同的只是選擇。我們不難想象有多少人隨波逐流,日夜抓拾碎片,不忌粗拙,解除寂寥。但一定有一些人避開嘈雜,退回閉塞的角落,關閉魔器,享受書香。他們甚至要在不同的紙質印刷物中再加挑選,對字體和紙張有一番權衡,以便有最好的享用。就這樣沉迷其中不能自拔。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讀者。
對于經(jīng)典而言,紙質閱讀是一種標配。經(jīng)典是由當代寫作一點點積累下來的,所以經(jīng)典也不能取代當代寫作。經(jīng)典之路如果不能與當下交接,也會走入迷途。好的寫作者一定與經(jīng)典對話,好的閱讀也是如此。現(xiàn)代科技催促我們尋找時尚,其實是犯了大錯。將經(jīng)典放在手邊,它們常讀常新。
08
人是一種奇怪的生物,最容易遺忘,一二百年過去就感到遙不可及了,認為那時的書也十分老舊。追逐國內外最新的流行物,以新為好。藝術恰恰相反,它們并不是越新越好,而要依賴時間的檢驗和甄別。時下的藝術經(jīng)過時間之水的沖刷,至少過去一個世紀才會凸顯出來。精神和藝術的歷史,一二百年真的不算長,也不過歷經(jīng)兩三代人。我們遺忘了十九世紀前后那些經(jīng)典,更不要說再早一些的,多么可悲。這實際上已經(jīng)是離我們最近的積累了。《詩經(jīng)》《楚辭》之類的作品以千年計,也沒有顯得特別遙遠。這么快就疏離了人類的杰出創(chuàng)造,怎么能令人信賴?怎么能積蓄偉大的文明?不可能。
被眼前的時新強烈地吸引,其實其中絕大部分只是泡沫,是光線下的泛光。某個時代人類的創(chuàng)造力突然破掉一個基線、一個局限和概率,產(chǎn)生出山一樣的杰作,是不可能的。參與者增多,理論上發(fā)生奇跡的概率可以提高,但一個民族一個時代,真正意義上的偉大作家和作品,一百年也就那么多,不會更多。縱觀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史,幾千年下來,以一百年為最小單位,一個世紀也不過如此,這是古老的規(guī)律。網(wǎng)絡時代的參與人數(shù)空前,卻未必能打破人類的歷史紀錄。百年之內關于精神和藝術的結論,無論怎樣鑿定有聲也會大打折扣,懷疑和挑剔在所難免。
即便那些已成定論的文學藝術經(jīng)典,也要經(jīng)過后人多輪選取,接受沒完沒了的質疑。像《在路上》《尤利西斯》這一類,像畢加索后期的創(chuàng)作,許多人認為它們實在被高估了。
寫作的人多了,也未必是寫作的大時代
《夢》又稱《在紅色安樂椅上睡著的女人》,畢加索,1932年
不要以為參與藝術的人多了,就一定是藝術的大時代。隨著消費主義、娛樂主義、物質主義的盛行,參與者的數(shù)量和品質,還有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,都會受到影響。以某些淫書為例,它們作為禁書,一致判為有害人類文明,卻在網(wǎng)絡時代受到推崇。許多類似的書都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評價,就此可以明白一個時代的偏嗜。有人強調它們的“認識價值”,但這里或可反問:這種價值能夠獨立并代替其他?另外,所有的人間大惡都有很大的“認識價值”,我們卻不會拿來審美。
今天,對精神敘事保持一種敏感的、更高的要求,是至為重要也是至為困難的。文學不能走向物質化和娛樂化,它畢竟不是可樂也不是漢堡。我們每天被各種荒唐離奇的信息、無數(shù)悲喜交集的事件所淹沒,正常的情感已經(jīng)被消耗得差不多了。文學即便一再提高自己的分貝,哪怕變得聲嘶力竭也無濟于事。數(shù)字荒漠中,悲慘的不覺得多么凄愴,奇跡也懶得贊嘆,神經(jīng)刺激過度了。也正因為如此,當今的文學究竟該怎樣書寫,就變成了一道費解的難題。精神的起伏跌宕,情感的兩手顫抖,不可忍受無比喜悅、夜不能寐的愛與恨,仿佛都不再動人了。
毀滅情感和自尊的高科技加物質主義,走到了一個極處且無法遏制。作為文學,尾隨就是墮落,就是一錢不值,類似的文字不讀還好,越讀越亂,引起厭惡,覺得卑賤。一個民族擁有這樣的文學才是真正的不幸。
我們曾經(jīng)專注于精神,寫人的失敗、勇敢和抵抗,寫人的尊嚴。人受到侵害之后多么痛苦不安,他們退于絕地,日日獨思。而今,僅僅獨坐沉思當然不夠,且起而做工,著手從未有過的復雜而艱巨的事項吧。
聲明: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容,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,均為采集網(wǎng)絡資源。如若本站內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益,可聯(lián)系本站刪除。